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ngines for large commercial airplane are being developed closely, and the tests for main components and the whole engine are being conducted massively in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emission combustors,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ypical R&D path of a civil engine combustor, 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test technologies of single cup, multiple cups and full annular combustors, in which the main test subjects, test process, instrumentation, key points and common issues have been summarized. At the same time, by making a comparison of test pressure/temperature, instrumentation, test abundance and perspectivenes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by summarizing of Chinese civil combustor test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the paper gives reference to the domestic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s of low-emission combustor research, test facility construction, measure-ment enhancement and gap fil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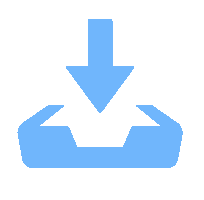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